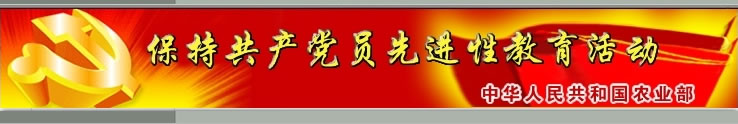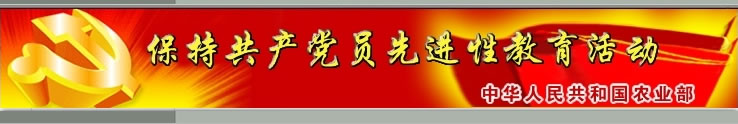贾继增同志于1970年参加工作,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考入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2年到中国农科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后改称作物科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他热爱祖国、热爱党,心系农业、情系农民,热爱作物品种资源研究事业,创造出了一流业绩。他作为主持人或主要完成人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集体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他先后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国家“五一”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先进农业科技工作者”、“农业部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贾继增同志是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共产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973”(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一
贾继增同志是从事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工作的。
种质资源研究是作物育种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在这一领域,他很快了解到,我国有丰富的作物基因资源,仅建在农科院的国家种质库就保存有33万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这一优势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在高科技领域,“星球大战”广为人知,而许多人不知道的“基因大战”也已悄然而至。许多重要的优良基因存在于种质资源之中。然而,目前种质资源是没有知识产权的,只有从中发现的基因进行专利登记后才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贾先生深知,世界范围内的基因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发达国家及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技术,正加紧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种质资源中鉴定与克隆基因,然后将其转变为他们手中的专利,高价卖给发展中国家,甚至以此来卡我们的脖子。
他认为,种质资源工作者应该重点进行种质资源新基因的发掘与种质创新。为此,近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他和老师、同事、同行先后进行了“国家重大科学工程”、“973”、“863”、“小麦功能基因组”等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申请。由他和张启发院士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通过5年的努力,已经构建了水稻、小麦和大豆三大作物的核心种质,初步发现了我国三大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对于这三大作物的遗传育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1992年开始,他就忙着筹建我国第一个作物种质资源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开启了基因资源学的研究工作。正是由于他和他的老师董玉琛院士及同事们的努力工作,1996年,农业部批准了作物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项目;2003年,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农业部的大力支持下,一个投资1.4亿元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装备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实验室建成并投入使用。据农业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领域第一个重大科学工程。这一成就对于提升我国作物基因资源研究与开发的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10多年来,在我国的种质资源研究方面,他开拓出了基于基因组学的种质资源研究新领域,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构建了高效发掘新基因的技术体系,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新基因;创立了高效的种质创新技术路线,创造出一大批优异新种质,比如,他们培育的抗白粉病优异新种质可在较长的时间解决我国小麦白粉病抗源缺乏的问题;开发出一批小麦新型分子标记,结束了我国小麦分子标记依靠国外的被动局面;获得了近万条小麦全长cDNA(基因的主要部分),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获得小麦全长cDNA最多的国家。
二
这位心系农业、情系农民,热爱作物品种资源研究事业的农业科学家,1945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农村。青少年时期,由于家里生活很艰难,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吃过树皮、树叶,经受了艰苦环境的磨练。但象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从小就经受着爱国、爱民的教育,古代的诸葛亮、文天祥、岳飞,现代的董存瑞、雷锋、焦裕禄是他的学习楷模。
中学时代,他就立志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65年,他的3张高考志愿表填写的全是农业院校,后来如愿以偿地考进第一志愿—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但他入学不到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70年毕业后分配到陕西商洛一个山区中学当教师。那里条件十分艰苦,但凭着对农业科研的兴趣与爱好,他开始了自己的初级农业实验研究,小麦杂交育种、栽培实验,制作发酵饲料,什么都做,当时曾因此被评为县、地区的先进教师,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人帮”粉碎后,恢复了高考与研究生制度。1979年,他考入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在我国著名的小麦品种资源专家董玉琛、丁寿康研究员指导下从事小麦品种资源研究,正式走上了农业科研的道路。
有人说,他的生活和学术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可是只有他最清楚自己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1992年,47岁的贾继增主持863项目时还是助理研究员职称,这在当时全国都是少见的。他也曾为此苦恼过,但他劝慰自己,科研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应首先把大事做好,不要因小失大,大事做好了,对人民、对自己都有好处。
参加工作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抓紧时间,勤奋工作。有人问他,你这样拼命工作累不累。他说,也累,也不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但对于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他多年来苦恼的是自古忠孝难两全。
采访贾老师的时候已经临近春节了。他说,他的父母亲去世早,岳父、岳母现在都是80多岁的人了,近10年来他仅去看过他们1次,今年春节又不能去看望二老,由爱人和儿女代看望。因为一篇文章已拖了半年,必须尽快完成,不然国外抢先发表,就可能前功尽弃。由于整天忙于工作,家里的事他很少管。他的两个孩子都是他爱人一个人带大的。他爱人操持家中大小事物,至今他老家有事来人也都是直接找他爱人而不找他。他动情地说,这么多年来自己欠下的情分太多了,欠父母的、亲戚的、同学的、同事的、朋友的。这些他都记在心里,有些他已无法偿还,有些等退休后还有机会偿还,对祖国和亲人,更多的只有以工作来偿还……
三
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严谨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率真的性情中人,常会做出令一般人意外的事情。而在实际工作中,他的率真和执着正是他取得卓越成就的源动力之一。
早在1985年,国家七五计划开始的时候,当时种质资源攻关项目没有将优异种质资源列入其中,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忧心忡忡:这样重要的项目为什么没列上?当时贾继增是硕士刚毕业,血气正旺,就写了立项建议书,找所长、院长“理论”,院里说这是农业部定的,他就到农业部与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理论”,当时的那位领导感到很突然,并批评他说不该为这件小事找领导。贾继增觉得自己是为了国家的科研事业,又不是为个人的事情,所以就委屈地哭了,那位领导见到这种情况,就放缓了口气,听他讲完,并收下了项目建议书。后来这个项目得到了资助。当然,这个结果与他找领导“理论”是否有关,不得而知。但他从国家科研实际的需要出发,以科研任务为己任的精神和气质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同事和学生。
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派到墨西哥的国际小麦玉米中心进修3个月。可是,没到3个月,安排的进修就结束了。由于正值5月初,是北京小麦做杂交的季节,他惦记着家里的实验,就提前一个月回国了。当时中国人对国外的好奇心远比现在要强烈,许多人出国总是要尽可能多待一些时间。他回来后,所领导见到他很意外,得知情况后高兴地说:“派你这样的人出国真让人放心!”
1990年,他在《Biotechnology(生物技术)》杂志上看到美国康耐尔大学一位学者发表的介绍分子标记技术的文章,敏锐地意识到这项技术将对未来的作物种质资源与作物遗传育种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就在这时,所里有一个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的出国进修名额,并把这个名额给了他。当时,单位准备派他去美国,但他考虑到自己是搞小麦种质资源的,而当时英国剑桥实验室在小麦分子标记技术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他提出要么去该实验室进修,要么就放弃出国。后来他如愿到剑桥实验室进修时,该实验室给他的工作是绘制小麦第6部分同源群连锁图。这是一个人一年的工作量,但他在一年的时间内除了完成这一项目外,还完成了抗白粉病基因的分子标记及从国内带去的小麦外缘染色体鉴定两项科研项目,工作量比两个人正常的工作量还多。他每天9点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或10点,有时甚至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周末和节假日除了去商店采购一周的食品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实验室的一些外国人常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是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年工作365天。”
1992年,一年多的进修时间结束了。当时他有三种选择:回国、转读博士学位、应聘到国外其他单位工作。那个时候,分子标记在国际上正热,招聘此类人才的广告随处可见,有了英国剑桥实验室的工作经历,有该实验室主任的推荐信,在当时找工作是很容易的,但他知道国家的科研项目正需要他的归来,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那个时期,别人回国时常常是为家庭带回国内稀缺的电器产品,而他带回的却是科研和实验用的东西。1992年5月,他带着沉重的行李箱从英国回来,里面装的都是文献资料,还有一个大干冰盒,里边装满了做实验用的各种试剂药品。因为有了这些之后,回国后就可立即开展实验。之后他又多次出国,每次回来都带回大批的试剂、药品、甚至仪器,这些药品有些是国外赠送的,有些是从国外购买的。几年来,他带回来的仪器、药品就为实验室节省了十余万元开支。
别人因此褒奖他是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报效祖国,他说“报效祖国”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而他只是做了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他谈到1998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参观时,远远望见在美丽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尊我国特有风格的鼍龙纪念碑,在西方风格的建筑群中十分突兀。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竖立的,碑文大意是,在祖国遭到日寇侵略的危急时刻,他们将投笔从戎,回国参加抗战。贾老师感慨地说:“留在世界最高水平的学府,还是走向随时都有失去生命可能的战场,对个人来讲那是一个有多大差别的选择啊?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他们相比,我们所做的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能够做到的还有更多!”
四
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贾继增同志还充满人文关怀的团队精神,是科技协作的组织者。他所领导的实验室,包括职工、学生、临时工,总共有60多人,其中学生和临时工多数远离家人。他认为,他们都为实验室完成科研任务而忙碌,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他们的劳动都应该得到尊重。
为了给实验室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也出于对每一位同志的关怀,贾继增同志决定给室里的每一位同志过生日,生日礼物包括一张全体人员签名的生日卡和一小盒鲜花,礼物虽小,但是能让每一位工作人员感到集体的温暖,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平时,不管是职工还是学生病了,他都关怀备至,如果住院就上医院看望。贾继增同志自己分房装修的时候没有时间管,天天照常加班加点工作,而为同事的房子却花费了很大精力。比如,孔秀英博士分房时出国在外,贾继增同志到所里找领导,到院里帮助联系,忙前忙后,终于帮她解决了。
贾继增老师课题组的博士生刘越说,她和同学们至今忘不了2003年4月底,非典开始在北京蔓延时的情景。当时有不少同学人心惶惶,有的想回家,有的害怕得不知道做什么好。此时正值小麦开始杂交的季节,为了便于管理和有效地开展工作,贾老师对他们说,试验田里空气新鲜,到麦田做小麦杂交实验是预防非典的好方法。
贾老师身先士卒,亲自带领同学们到试验田去做小麦杂交实验。这时,实验室的一名女学生有点发烧,贾老师立即向所里汇报了情况,并且马上采取措施,让她单独居住,保证宿舍通风,又有人按时送饭。第二天清晨,贾老师早早就去询问学生情况怎么样,发现没有明显的好转,当即报告院门诊部,大夫经过初步检查,仍不能排除疑似症状,决定立即送发烧门诊,希望单位派一个人一起去。当时,如果学生确诊为非典,同去的人也肯定得被隔离。贾老师却毫不迟疑地说:“这是我的学生,我应该去。”院里派了一辆非典专用车送贾老师和那位学生一起去了医院。同学们都紧张得很,因为就连接送非典病人的车从学院南路经过时都要通知关闭院大门,禁止出入。当检查结果排除了非典疑似,贾老师带着那个女学生平安返回时,全体实验室人员紧紧把他们围在中间,又叫又跳,沐浴在患难见真情的激动和幸福之中。
贾老师把学生当作子女一样关心备至,却经常忽略应该给予自己孩子的父爱。有一年的圣诞节前夕,他的女儿制作了圣诞树、买了一只漂亮的花靴子挂在墙上,并告诉父亲晚上一定要把给她的圣诞礼物放在圣诞树下,放在靴子里。但等贾老师从实验室回家时,已晚上11点多,商店都已关门。想着女儿期盼的目光,他真感到内心有亏,回到家里,只好给女儿写了一封短信,放在靴子里。信上祝愿她身体健康,学习进步,未来生活幸福,事业有成。这些词语固然能够表达一个父亲的爱和祝福,但对于女儿那并不过分的具体要求来说,此时却显得那样的苍白和单薄……他的女儿从此再不愿给这个“工作狂”一般的父亲,提出任何烂漫的要求了。
贾老师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心血都倾注到了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的建设上。除了日常业务外,他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包括学术报告,体育比赛等,不仅增加了实验室各课题组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促进了成员之间的协作。他与他的团队已经连续两届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他和同事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业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前面的路还很远,肩上的担子还很重。贾老师说:“作为农业科研领域国家队成员,我们的使命就是在世界上占领我们应该占领的一席之地。我们的目标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将我国的种质库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库,使其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与农民致富的‘基因银行’;为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尽快走在世界前列做出应有的贡献!”